
最高统治者是谁很重要,而归根到底仍然是眼巴巴地期待着好皇帝,不幸的是好皇帝没那么多。
人类历史中,从没有中断过对旧事物、旧做法、旧秩序及旧制度的局部或根本性调整。有时是改掉不合理的,使社会逐渐完善,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;当社会矛盾激化,而阻力过大或者改革各方无法形成妥协时,就爆发了革命。在古代历史上,改革即便成功了,社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,最终往往也很难逃脱“人亡政息”的命运。
中国最早的法制化改革是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发起的“铸刑鼎”的改革。改革的第一年,由于人们因循守旧,也触动了某些人的私利,所以人们群起而攻之,恨不能把子产杀了。但经过三年,子产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大大超过以前的实惠,人们对子产由怨恨变成了拥护,甚至开始歌颂他:“我有子弟,子产诲之;我有田畴,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,谁其嗣之!”意思是,子弟受到子产的教诲,田地产量增加了,生活变好了,百姓自然唯恐这样的好官早死,怕他死了以后没有人坚持他的好政策。

子产

铸刑鼎
子产,春秋时期郑国人,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堪称“春秋第一人”。子产从政后,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。其中“铸刑鼎”是子产改革的一件标志性事件,打破了古代中国的法律秘密主义。
子产的改革本来是成功的,成效是巨大的,却遭到了晋国叔向的指责,说“民知有辟,则不忌于上”。意思是说,国家法律应该保密,不应该公之于众,因为一旦平民百姓也知道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,就不会俯首听命于官员贵族,这些人也就失去了威严;而人们知道了法律,就会维护自己的权益,与官府与他人依法进行争辩,就会造成种种争端,犯法的人也就会多起来。叔向还预言郑国就要完蛋了。在子产改革七八年后,又有突出成就显现出来的时候,叔向还闭眼不看事实,一味指责子产不该公布法律内容而放弃“礼”的说教。对这种顽固守旧、盛气凌人的做法,子产不客气地回答说“吾以救世也”,与后世王安石“天命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的改革决心如出一辙。事实上,到公元前522年(郑定公八年)子产去世,郑国一直被治理得很好,周旋于晋楚两霸之间,处置得宜,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和尊严。然而子产死后,郑国渐渐丧失优势,走向没落,最后被韩所灭。
战国末期,法制化改革更是成为社会主流。其中最成功的当属商鞅变法。变法的核心是将百姓的利与国家的利结合在一起,为社会增添了活力,使秦国从弱国变为了最强的国家并消灭六国而一统天下。但十几年后,秦朝就灭亡了。
历史上一直不乏有识之士,有责任、有智慧、有担当,但即便有的改革成功了,到最后也没有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。张居正是对专制社会弊端进行改革的集大成者。到了明朝,中央集权以及君主专制日益加强。但是对于权力,皇帝不能自己都行使,又对谁都不信任,只能依靠身边的太监,而太监既没有知识上的顾忌,也没有道德上的束缚,还没有“后顾之忧”,一旦把持朝政,就会搞得一团糟。
到了明朝末年,战争频发,民不聊生,总体而言,内忧外患。1568年张居正着手改革,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第一,“省议论”。因为当时很多人只动嘴,不干事,没干先说难,干啥事都觉得难。因此改革要求少说空话,多干实事。第二,“振纲纪”。要整肃纲纪,严明法律,做到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。第三,“重诏令”。当时权力一收就死,一放就乱,特别是地方官员徇私枉法。于是改革要求令行禁止,提高效率,地方得听中央的科学决策,不能说一套,做一套。第四,“核名实”。当时社会阶层严重固化,能够进入体制当官的不是“官二代”就是“富二代”,其中很多人不学无术,因此改革规定进入体制的人也要考试,选拔杰出人才。第五,“固邦本”。轻徭薄赋安抚民众,重税解了一时之渴,种下的则是长期的苦果。国家要把一部分利益让渡给社会,减轻老百姓的负担,适度藏富于民。第六,“饬武备”。张居正发现在那个时代,政权不是依赖于老百姓而建立起来的,思想上依赖于“神化”,现实中依赖于武力。当时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稳定的主要依靠,往往比地方腐败还严重,战斗力大幅度下降。因此张居正改革军事,好好训练,准备打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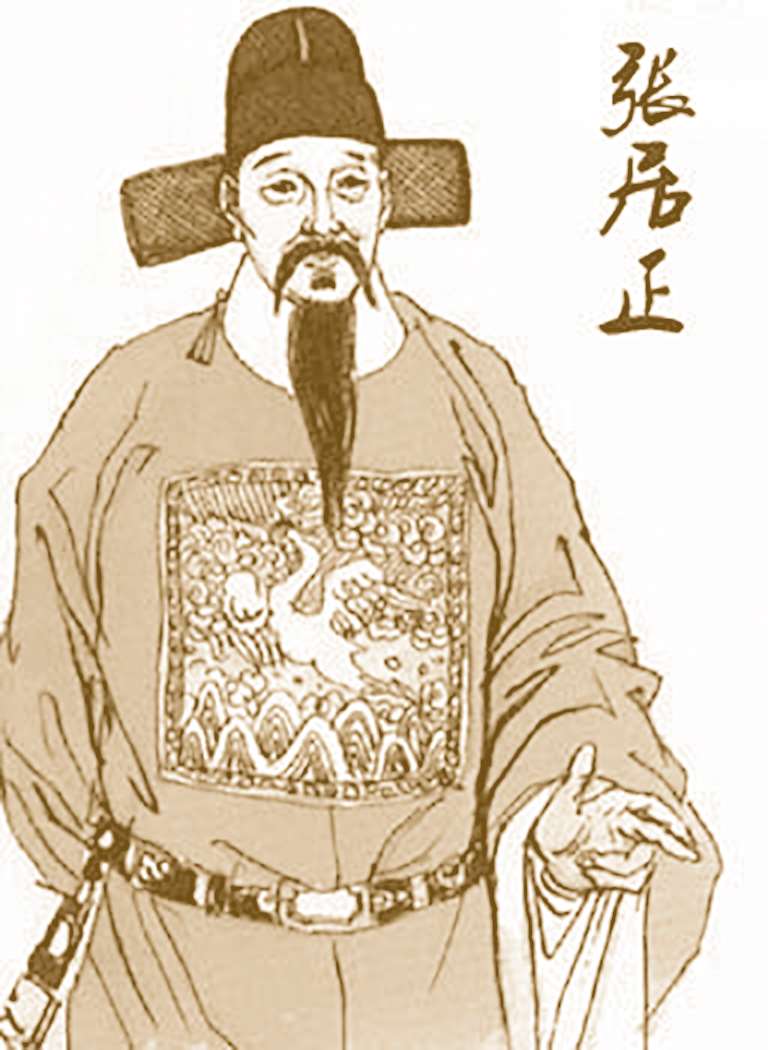
张居正,字叔大,号太岳,汉族,幼名张白圭。江陵人,时人又称张江陵。明朝中后期政治家、改革家,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,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“万历新政”。
在张居正的改革下,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,二三十年没打大仗,缓和了社会矛盾,改变了明朝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。然而张居正一死,他的改革制度就被推翻,他得罪的人挖了他的祖坟,杀了不少他家的亲戚和支持者,明朝也慢慢走向灭亡。张居正改革的失败,与官员腐败并已形成利益集团,不愿让出既得利益,也没有远见,看不到改革有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。改革的时机一旦错过,百姓由充满期待到不再相信政府能够改革,最后出现改朝换代的局面。
是法治不行还是法治有漏洞?周期率作为历代王朝的铁律怎么能够被打破?我们看到,“人亡政息”的关键在于改革一直是依赖于人,特别是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,这些举措也没有通过反映人民利益的法律固定下来,没有所谓的人文启蒙、权利意识觉醒,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,没有民众参与并支持,更没有涉及王权的改革。而人天然具有易变性,人变了,规矩也就变了。